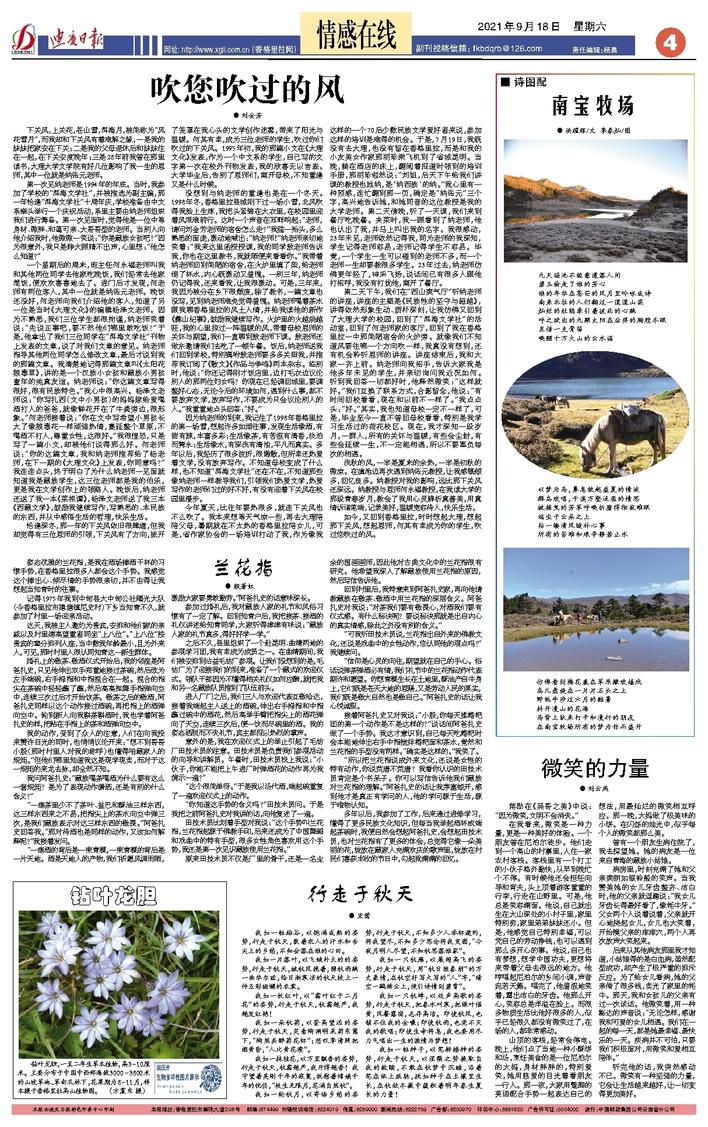
吹您吹过的风
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被简称为“风花雪月”,而我却和下关风有着难解之缘,一是我的妹妹把家安在下关;二是我的父母退休后和妹妹住在一起,在下关安度晚年;三是28年前我曾在那里读书,大理大学文学院有好几位影响了我一生的恩师,其中一位就是纳张元老师。
第一次见纳老师是1994年的年底。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洱海文学社”,并被推选为副主编,那一年恰逢“洱海文学社”十周年庆,学校准备由中文系牵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系里主要由纳老师组织我们进行筹备。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微胖、和蔼可亲、大哥哥型的老师。当别人向他介绍我时,他微微一笑说:“你是藏族女孩吧?”因为很意外,我只是睁大眼睛不出声,心里想:“他怎么知道?”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班主任何永福老师叫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去他家吃晚饭,我们经常去他家混饭,便欢欢喜喜地去了。进门后才发现,何老师有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纳张元老师。晚饭还没好,何老师向我们介绍他的客人,知道了另一位是当时《大理文化》的编辑杨泽文老师。因为不熟悉,我们三位学生都很拘谨,纳老师笑着说:“先说正事吧,要不然他们哪里敢吃饭?”于是,他拿出了我们三位同学在“洱海文学社”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说了对我们文章的意见。纳老师指导其他两位同学怎么修改文章,最后才说到我的那篇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叫《太阳花 狼毒草》,讲的是一个汉族小女孩和藏族小男孩童年的纯真友谊。纳老师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民族特色。”我心中很高兴。杨泽文老师说:“你写扎西(文中小男孩)的妈妈嫁给爱喝酒打人的爸爸,就像鲜花开在了牛粪旁边,很形象。”何老师接着说:“你在文中写希望小男孩长大了像狼毒花一样顽强热情,蔓延整个草原,不喝酒不打人,尊重女性,这很好。”我很惶恐,只是写了一篇小文,却被他们说得那么好。何老师说:“你的这篇文章,我和纳老师推荐给了杨老师,在下一期的《大理文化》上发表,你同意吗?”我连连点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纳老师一见面就知道我是藏族学生,这三位老师都是我的伯乐,更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晚饭后,纳老师还送了我一本《菜根谭》,杨泽文老师送了我三本《西藏文学》,鼓励我继续写作,写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并从中感悟生活的哲理,快乐生活。
恰逢深冬,那一年的下关风依旧很肆虐,但我却觉得有三位恩师的引领,下关风有了方向,拔开了笼罩在我心头的文学创作迷雾,带来了阳光与温暖。何其有幸,成为三位老师的学生,吹过你们吹过的下关风。1995年初,我的那篇小文在《大理文化》发表,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在校外刊物发表,我的欣喜无以言表。大学毕业后,告别了恩师们,离开母校,不知重逢又是什么时候。
没想到与纳老师的重逢也是在一个冬天。1998年冬,香格里拉县城刚下过一场小雪,北风吹得我脸上生疼,我把头紧缩在大衣里,在校园里迎着风艰难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老师,请问刘金芳老师的宿舍怎么走?”我猛一抬头,多么熟悉的面庞,激动地喊出:“纳老师!”纳老师亲切地笑着:“我来这里函授授课,我的同学敖老师告诉我,你也在这里教书,我就顺便来看看你。”我带着纳老师回到简陋的宿舍,在火炉里填了柴,给老师倒了杯水,内心既激动又羞愧。一别三年,纳老师仍记得我,还来看我,让我很激动。可是,三年来,我因为被分在乡下很颓废,除了教书,一篇文章也没写,见到纳老师难免觉得羞愧。纳老师喝着茶水跟我聊香格里拉的风土人情,并给我读他的新作《彝山纪事》,鼓励我继续写作。火炉里的火越烧越旺,我的心里掠过一阵温暖的风,带着母校恩师的关怀与期望,我们一直聊到敖老师下课。敖老师还做东邀请我们去吃了一顿午餐。饭后,纳老师送我们回到学校,特别嘱咐敖老师要多多关照我,并推荐我订阅了《散文》《作品与争鸣》两本杂志。临别时,他说:“你还记得刚才饭店里,边打毛衣边议论别人的那两位妇女吗?你现在已经调回城里,要调整好心态,无论今后的环境如何,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放弃文学,放弃写作,不要成为只会议论别人的人。”我重重地点头回答:“好。”
因为纳老师的到来,我记住了1998年香格里拉的第一场雪,想起许多如烟往事,发现生活像酒,有甜有辣,丰富多彩;生活像茶,有苦涩有清香,淡泊而隽永;生活像水,有深浅有清浊,平凡而真实。多年以后,我经历了很多波折,很懒散,但所幸还热爱着文学,没有放弃写作。不知道母校变成了什么样,也不知道“洱海文学社”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些像纳老师一样教导我们,引领我们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老师们过的好不好,有没有迎着下关风在校园里漫步。
今年夏天,比往年要热很多,就连下关风也不么吹了。我本来想等天气凉一些,再去大理陪陪父母,暑期就在不太热的香格里拉陪女儿,可是,省作家协会的一场培训打动了我,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70后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培训是难得的机会。于是,7月19日,我既没有去大理,也没有留在香格里拉,而是和我的小友美女作家那丽珍乘飞机到了省城昆明。当晚,躺在酒店的床上,翻阅着报道时领到的培训手册,那丽珍忽然说:“刘姐,后天下午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也姓纳,是‘纳西族’的纳。”我心里有一种预感,连忙翻到那一页,确定是“纳张元”三个字,高兴地告诉她,和她同音的这位教授是我的大学老师。第二天傍晚,听了一天课,我们来到餐厅吃晚餐。夹菜时,我一眼看到了纳老师,他也认出了我,并马上叫出我的名字。我很感动,23年未见,老师依然记得我,同为老师的我深知,学生记得老师容易,老师记得学生不容易。毕竟,一个学生一生可以碰到的老师不多,而一个老师一生却要教很多学生。23年过去,纳老师仿佛更年轻了,神采飞扬,说话间已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我没有打扰他,离开了餐厅。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西山爽气厅”听纳老师的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民族性的坚守与超越》,讲得依然形象生动、质朴深刻,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大理大学的校园,回到了“洱海文学社”的活动室,回到了何老师家的客厅,回到了我在香格里拉一中那简陋宿舍的火炉旁。就像我们不知道风要往哪一个方向吹一样,我真没有想到,还有机会聆听恩师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我和大家一齐上前。纳老师向我招手,告诉大家我是他多年未见的学生,并亲切询问我近况如何。听到我回答一切都好时,他释然微笑:“这样就好。”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合影留念,他说:“有时间回校看看,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点点头:“好。”其实,我也知道母校一定不一样了,可是,毕业至今一直不曾回母校看看,特别是我学习生活过的荷花校区。现在,我才深知一段岁月,一群人,所有的关怀与温暖,有些会尘封,有些会延续一生,不一定能相遇,所以不要辜负每次的相遇。
浅秋的风,一半是夏末的余热,一半是初秋的微凉。在滇池边再次遇到纳张元教授,让我感慨颇多,回忆良多。纳教授对我的影响,远比那下关风还深远。纳教授与恩师何永福教授,在我读大学的那段青春岁月,教会了我用心灵辨析真善美,用真情诉诸笔端,记录美好,温暖宽容待人,快乐生活。
如今,又回到香格里拉,时时想起大理,想起那下关风,想起恩师,何其有幸成为你的学生,吹过您吹过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