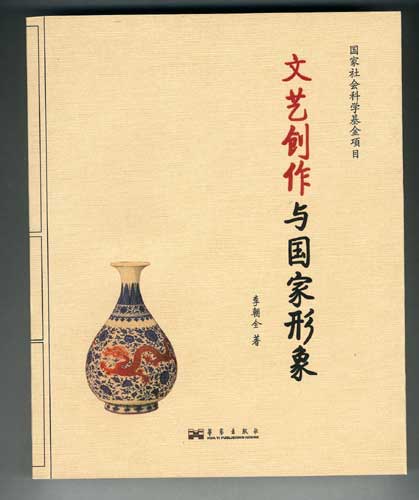|
本文选自李朝全所著《文艺创作虞国家形象》一书。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李朝全授权新华网教育频道百家讲堂栏目刊发。本文观点与本网观点和立场无关。 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流传甚广、迎合读者期待与需求的作品,对西方人形成关于中国的印象、感受、认识等起到很大作用。西方人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有关中国主题的,既有被译介过去的中国作品,也有由西方人直接创作的。 一、西方人通过中国的文学艺术了解中国 中国人使用的汉字,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口语和书面语之一,是"最复杂、最难懂、最笨拙的思维工具"。西方人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大多基于西人的译作,而这种译作因对"汉语"带有严重的误读必然存在诸多的缺陷。 西方人阅读中国作品,主要目的是要借此了解中国人历史和现实的生活状态、奇特的社会习俗。儒莲说:"最好是翻译中国的作品,……这些作品能使我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宗教、习惯、风俗和文学。" 中国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对生活和格调的"乏味夸张",一切事情都讲究一定的仪式,都有严格的礼俗规范,人物的生活矫揉造作、循规蹈矩。西方人由此认为:现实中的中国人可能也是呆板不化、亦步亦趋、中规中矩、缺乏血肉情感的。 在西方人眼中,《金瓶梅》讲述的是"商人西门庆和他的六个老婆的故事,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该书内容的主要部分";《红楼梦》则讲述"一个荣耀高贵的家庭被剥夺了长期以来所享用的皇帝恩赐而最后衰落的故事"。这类题材的小说带给西方读者的印象是: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男人都妻妾成群,女人不仅要服侍丈夫,还要照顾公婆、小叔、妯娌、小姑和孩子们,她们妒忌心强,相互勾心斗角。而小说角色流行使用敬语和谦词,则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国人生性做作、虚伪的表现。 对于中国戏剧,诸如《琵琶记》、《汉宫秋》、《赵氏孤儿》、《西厢记》,尽管西方人也承认这些作品剧情跌宕,细节优美,表现简洁、明晰、自然,风格独特,对了解中国习俗和生活很有价值,中国人演技超凡,灵活敏捷等,但是,"总体而言,他们认为中国戏剧粗俗、造作"。中国人的幽默被认为是猥亵下流,中国人的笑话则鄙俗不堪。? 对于中国诗歌,因为中国的诗人"内心深处没有太多的宗教激情可以宣泄",在表达超凡世界或上帝的意志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西方人认定中国诗人缺乏灵气和深度。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电影的接受,西方人热衷于发现"铁幕"后中国人僵化、落后、残忍、愚昧、野蛮不开化、专制不自由等负面特性,关注中国神秘的"功夫"、武侠、奇异而压抑的爱恋情感,注意的是其中所表现的各种独特的习俗。换言之,西方人是按需接受,从自己的接受心理定势出发来选择中国的文艺作品,并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加以阐释和理解。 (来源:新华网) 二、西方文艺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 法国文豪伏尔泰1755年根据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悲剧《中国孤儿》,把故事挪到了欧洲人感兴趣的蒙古族铁腕人物成吉思汗的时代,描写中华民族的儒家智慧与修养最终感化了这位少数民族的领袖成吉思汗,使他制止屠杀,成为贤明的一代君主。《中国孤儿》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中国式风格"的戏剧,采用的道具和布景都是"中国式"的,而其思想内涵则是欧洲人传统的思想。 在西方大部分作家的笔下,中国人被描绘成"可爱"却不大通人情、缺乏血肉情感的玩偶。家长总是满脑陈腐学问,满嘴孔孟之道,手握毛笔写个不停;年轻的新娘娇媚秀丽,天真无邪,打扮得如花似玉;而妇女们总是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之下,没有自由;她们的名字译成西文后便成了"金色的莲花"(金莲)、"冬季的樱花"(冬樱)之类,越发带给西方人矫揉造作的印象。而在西方小说中的中国人,则往往被刻画成活生生的"中国式风格"工艺品中的雕像。像哈罗德·阿克顿的《牡丹与马驹》一书中塑造的一对中国恋人,只是"两个会动的象牙雕像,两个灵巧的、精心制作的机器人",而中国则被描述成"一出常年不断上演的哑剧",从天坛到公开处决等百件事物总有人出于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围观。西方作品中的这些中国人物,又被西方作家赋以运用过分客套的敬语和谦词对话,而且使的是蹩脚的洋泾浜英语,平添了许多辛辣的嘲笑和讽刺意味,诸如欧内斯特·布拉默所写的Kai Lung(《凯隆》)的故事,狄更斯撰作的喜剧等。 在英国著名作家索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笔下,中国的高官被塑造成"腐化、无能而且肆无忌惮,他要扫除挡住他去路的一切障碍。他是勒索高手。他用最可恶的手段积累了一大笔家底。他阴险狡猾、残忍、报复心重,而且贪污受贿"。 对西方读者影响最广、最深的有关中国的小说,应数美国女作家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即赛珍珠(1892-1973)发表于1931年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于1932年获普利策奖金。1938年她因创作了描绘"中国农民的丰富多彩而真挚坦率的史诗"和"传记文学的杰作"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曾在中国生活、传教多年,晚年的政论主要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攻击共产主义。她是地道的"中国通",自称热爱中国,但她爱的是封建时代的旧中国。《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王龙的贫苦农民经历私营业主、家庭困难和矛盾纠纷,最后达到了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发迹。这个故事因为迎合了许多美国人自身的经历与阅读口味,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与共鸣,所以大受欢迎。但读者对其中的中国背景并不太在意,只留有模糊的印象。她的《大地》及随后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发表的《儿子们》、《分家》这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并未能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也未能反映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在其1957年发表的《北京来信》及1969年发表的《梁太太的三个女儿》中,则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情绪。 歌剧方面,意大利著名的歌剧作家普契尼撰作的《蝴蝶夫人》塑造的中国女人东方式的典雅、含蓄,压抑自己的欲望与情感的形象,在西方人代表的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逐渐变得开化大胆,敢于追求爱情,情感炽热、真挚。歌剧《中国公主图兰朵》则塑造了另一位富于个性的中国女子。 电影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中国女人一向被描绘成"花瓶式"的;中国男人则多为留长辫、穿长袍,中国古装戏里的人物。近些年来由于李安、吴宇森等一批华人导演以及成龙、李连杰等中国演员的加盟,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多被赋予中国功夫、武侠形象,人物的情欲都是压抑的、蕴蓄的,布景和道具、背景音乐等都是典型的"中国式风格":深山老寺,雕梁画栋,中国民俗等,集中展现的是一个古老、神秘、幽雅、怪异的中国整体形象。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齐1987年执导的《末代皇帝》正是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的电影方面的代表。 电影中的末代皇帝溥仪被作为中国人形象代言人,电影着重表现溥仪当上皇帝后被限制了自由到成为平民后恢复了自由的过程,表现中国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与扭变。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神秘、怪异的中国场景:表现红卫兵跳"忠字舞"的文革街头场景,具有纪录电影式的特征;慈禧"老佛爷"生活的空间,她的病榻被置于一个烟雾弥漫、佛像环绕的殿堂里。电影中许多细节描写也暗合西方人的欣赏心理,比如:小皇帝喜欢一张口就吸吮奶妈的乳头,揪心地叫喊"我要出去";那只溥仪幼时玩耍过的蝈蝈神奇地活过半个世纪,由绿色变成了褐色。电影通过对溥仪一生的描述,表现的是中国60年的历史,体现着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和文化的哲理性思考。其对神秘、古旧、怪异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其赢得西方读者,并一举摘取第六十届奥斯卡九项大奖的根本原因。 2000年,罗燕根据赛珍珠小说Pavilion of Woman改编、严浩执导的影片《庭院里的女人》,表现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及其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动人经历。女主人公吴太太被刻划成心思缜密、绵里藏针、秀美端庄的东方女性,她在美国教会医生安德鲁的启发引导下,逐渐从中国男尊女卑、相夫教子、三纲五常的囚笼中挣脱出来,自觉追求爱情,献身爱情。影片的场景也是中国式的:深宅大院、朦胧水乡,吴家花园里举行盛大寿宴、堂会,金水镇通电仪式上的烟花爆竹、中国大戏,旧中国沿河停泊岸边的花船,孩子们在水边捞莲藕、捉鸳鸯……所有这一切所呈现的正是一个遥远而陌生、古老而神秘、朴实而怪异的中国形象。(来源:新华网) |
西方人从文艺作品中读解到的中国形象
来源:香格里拉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5-12 10:39:46

频道精选
- 2024 年迪庆州新闻系列综合高级职称定向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区直通车:便捷出行,一站直达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区直通车:便捷出行,一站直达美景2024-09-05
- 张卫东到迪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开展调研2024-09-05
- 福彩代销者:增强责任意识 倡导理性购彩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庆人,这场活动需要您的参与!2024-09-04
- 积极参与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庆见义勇为”宣传募捐活动倡议书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