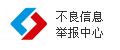研学探秘 丈量成长

“叮叮叮——”凌晨5点半的闹钟像一把钥匙,拧开了夜色的大门。我裹着羽绒服冲出宿舍,抬头望见银河如倾泻的轻纱,正沿着雪山的轮廓静静流淌。那个困在试卷与公式里的我,仿佛被这无边的浩瀚轻轻托起。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研学,或许不是带着预设的问题出发,而是怀揣着一颗好奇的心,任由自己被这份未知一把拽进黎明。
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雾气像不肯起床的淘气孩子,赖在车窗上不肯走。在引擎的低吼与颠簸中,海拔表的数字已从3200米跃升至3800米,手指有些发颤,胸口像塞进一头乱撞的小鹿。我忽然懂了,山提出的问题,唯有脚步才能成为它的标尺。
八点半,我们到达石卡雪山脚下。藏语里,“石卡”意为有马鹿的山。可此刻,马鹿不见踪影,只有一条被冰霜浸透的木栈道,像一条银灰色的丝带,飘向云里,我迈出第一步,鞋底踩碎冰珠,“啪嗒”一声,像给清晨点了个赞。
起初,队伍像一条彩色的哈达,在林间飘动。半小时后,队伍断成几截,颜色变得越来越丰富:不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有人把外套围在腰间,有人哼着小调。我落在队尾,却意外捡到了“宝贝”:一只被风吹落的松果,鳞片张开像小火箭。我蹲下来,听见它内部传来“沙拉沙拉”的响声,那是种子在为一次尚未启程的飞翔欢呼!我把松果放进背包侧袋,继续向前。
再往上,山路愈发陡峭曲折,每一步都令人胆战心惊。我们排成两列,像两串摇摇欲坠的字母,被山风肆意撕扯。每向前一步,脚下的石子便滚动着发出抗议。我的脚步越来越慢,心头却始终压着一个念头:不能给班级丢脸。正是这份责任感,支撑着我负重前行。可心底仍有一个声音在轻轻问:我真的能把自己完整地带到山顶吗?
答案最终出现在一只手中。就在我咬牙试图“大步”向上时,身旁一直默默相伴的好友竟毫不犹豫地把消防员帮助她的机会让给了我。而她大口大口地呼着气,脸上有一层薄薄的细汗,眼睛弯弯的像月牙一般,坚定地说:“加油!”她把“帮助”二字写得比任何课本上的文字都更深刻、更响亮。
终于,在4500米的垭口,风像一把巨大的梳子,把云雾梳成千丝万缕的银丝。雪山露出真容,阳光打在上面,反射出一道柔软的金线,像给地球戴上了一条亮晶晶的项链。
午餐是自热米饭。刚取出餐盒,天上就飘起了小雪。有人说,这是圣洁的象征,是大山以纯洁的方式在欢迎、在守护我们。带队的老师指向远处一片裸露的岩层,对我说:“看见那条灰色的线了吗?那是两亿年前的海底。我们今天脚下踩的,曾经是鱼游过的脊背。”原来,时间也有脚印,只不过它踩过的地方,都成了山。记得外婆曾对我说过:“把山装进行囊,你就再也走不丢。”
下山的路比来时轻松不少。我们排成纵队,像一串被山风串联的感叹号。我将那只松果重新掏出来,悄悄放回一棵树下,让它继续等待属于自己的风。回头望去,我们的脚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云端,仿佛为雪山钉上一条会发光的拉链——拉上去,是少年的轻狂;拉下来,是成长的重量。
(迪庆州民族中学初48班和鹏甜)
责任编辑:鲁茸只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