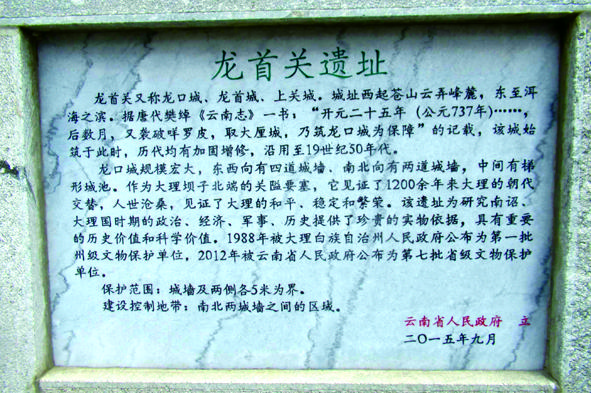盐 的 味 道
——史书中傈僳族与盐的故事
◆李贵明/文 张锦明/图
(上接3月20日 第四版)
杨国忠在朝廷得势后,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用人失察,举荐张虔陀担任云南太守。张虔陀依仗其与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私交时常索贿于南诏,南诏敬贡朝廷的金银土产也多被张太守据为己有。由于南诏常常难以完成张虔陀增税加粮、敬贡的号令,张虔陀虽然心有不快,但面对佣兵数万的南诏,唯一的办法也就是派人厉言辱骂一通作罢。这当然也使南诏王内心怨愤。南诏王与唐朝姚州太守张虔陀的关系并不见好。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天宝九年(750年)。野传南诏王阁罗凤率妻女赴唐朝剑南节度议事,途经唐朝姚州都督府时,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了阁罗凤的妻子。后南诏王派遣王毗奴、罗时牟苴率兵五千攻陷姚州杀死张虔陀。第一天一起喝酒的两个人,第二天不惜刀兵相见反目成仇,唐都督或自服孔雀毒胆丧命,或死于乱箭穿心,终成谜团无人知晓。唯一留给世间的事实是南诏和唐朝的关系由此瓦解。
南诏攻陷姚州杀死云南太守的消息传来,在杨国忠忙于征兵抓丁期间,愤怒的南诏军队已东进攻陷安宁城及盐场,扫除了唐朝设置在云南的大部分统治机构,直逼滇东。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唐朝调集八万军队分三路进军征伐南诏。此时,吐蕃也已经察觉到唐朝即将对南诏发起的进攻,为防唐军攻陷南诏乘势北进,吐蕃增兵腊普神川降域,率领浪穹、施浪和邆赕三浪诏族民施蛮、顺蛮枕戈待旦,“观衅浪穹”。唐军来势汹汹,鲜于仲通势必为张虔陀报仇,南诏王阁罗凤这下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为挽回与唐朝大军直接交战的局面,连忙派遣使者谢罪,说:“我将谢罪归还东进中所有的俘获物资、领地、人员和城池,撤师西回故地,恭请唐朝王师罢兵止械,撤旗东回。如果这样仍然不行,我只能率部投奔吐蕃,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许唐朝也不一定能够再统治云南。”率领六万大军的鲜于仲通此时不可能不战而退,不仅囚禁了南诏使者,还积极排兵布阵意欲一举攻灭南诏,诛王屠城。
当唐朝万众兵马到达洱海出口西洱河口时,南诏派遣使臣杨利急奔其北部的浪穹诏请求吐蕃出兵援助。此时,鲜于仲通已经摆开在西洱河龙尾关正面佯攻,秘密派遣王天运爬上苍山,试图两路夹击攻灭南诏都城的阵势。吐蕃神川御史伦若赞接到南诏使臣杨利的紧急求援后,察情通变,识破鲜于仲通计谋,率领铁桥城一带土著部落分师入救。神川御史伦若赞率部进入苍山伏击,阁罗凤正面迎击鲜于仲通。公元750年7月,伦若赞率领的吐蕃援军在苍山上伏击唐军成功,唐军将领王天运被临阵斩杀,次日将首级送至龙尾关高悬于南诏军队行辕门外,唐军军心大乱。与鲜于仲通对峙的阁罗凤命令段忠国乘机立即率部出击,双方大战三日,六万唐军被彻底击溃,鲜于仲通之子死于阵前,鲜于仲通趁夜逃亡。
此战之后南诏与吐蕃实际上已经形成军事同盟,为进一步加强政治联盟,南诏派遣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进入逻些拜访吐蕃,吐蕃也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南诏于公元752年改元为赞普钟元年。公元753年,唐朝军队再次卷土重来,派兵重置姚州,并任命贾颧为都督发兵三万试图进攻南诏,南诏和吐蕃神川驻军趁唐朝军队立足未稳再度大破姚州,贾颧被擒,三万唐军败溃。公元754年,唐朝派剑南留后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三路大军十万余人再征南诏,李宓总结了鲜于仲通苍山偷袭失败的教训,改为水路进攻,实施造船西渡洱海、水陆并进直捣南诏国都的策略。但是他在洱海东部的造船行动被南诏军队获悉,南诏王阁罗凤派遣王乐宽帅兵三百余人潜袭唐军造船工场,突袭造船之师,至“伏尸遍野”造船工场被捣毁。李宓只好绕道洱海北部准备从龙首关南下攻击南诏都城。公元754年6月,李宓率领十万唐军由北向南攻击至南诏太和城外围,由于洱海北部的土著部落视唐军为入侵者,孤军深入的唐军粮尽军旋,吐蕃神川都知伦依里徐从铁桥城再度及时赶到,双方内外夹攻,在上关一带发生惨烈大战,唐朝军队被吐蕃和南诏联军里应外合再次击败,将军李宓沉湖而死,十万唐兵覆没殆尽。这三次战争在历史上称为“天宝之战”,三战均以唐朝远征惨败告终。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留下了关于天宝战争的诗篇。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描述了天宝之战:“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六诏星居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李白《古风》写道:“渡沪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在《书怀寄南陵 常赞府》中又写道:“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沪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更加细致地描写了这场战争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
天宝战争后,唐朝陷入了安史之乱。他们的叛将安禄山正在联合回鹘、契丹、突厥等北方民族组成军队起兵攻击河北,唐朝由此无力再度组织远征南诏的军事行动。公元779年,异牟寻继位南诏国王。为了继续获得吐蕃的政治承认与军事支持,异牟寻一上任便积极建议吐蕃其立赞赞普攻击蜀中富饶地区,试图建立吐蕃“东府”。吐蕃赞普同意了“弟皇”异牟寻攻击蜀中的建议。公元779年10月,南诏出兵三万,吐蕃出兵七万,合计十万余众分三路攻击蜀中,中北两路由吐蕃军队负责,南路由南诏进军。但是吐蕃和南诏联军在大渡河、维州、茂州一带被李晟、曲环率领的唐朝精锐部队和蜀中“山南兵”击败。南诏和吐蕃在掳走蜀地近万工匠后各自返回。此次失败,使吐蕃赞普很不高兴。他认为南诏的向导误导了联军进攻路线,南诏先头部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将发起攻击属中建议的异牟寻从“赞普钟”地位降为“日东王”,意味着异牟寻从“弟皇”降为“地方王”。 对于这样的结果,异牟寻当然也心有不快。公元794年,吐蕃到南诏征兵一万攻击蜀地和北部的回鹘,已暗中与唐朝结盟的南诏王异牟寻同意先派三千士兵,至金沙江西岸的迪庆其宗、丽江石鼓一带时,南诏王异牟寻和唐朝将军牟皋派出尾随的上万联军里应外合突袭吐蕃,攻占吐蕃十六城,抓走五个吐蕃亲王献给朝廷,并一举斩断位于茶马互市和战略咽喉之地的神川铁桥。
为了夺取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居住区的盐井,瓦解长期归附吐蕃麾下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部落政权的威胁,南诏于贞元十一年(795年)年将三浪诏族民驱离洱海周围的高山平地,流放金沙江岸峡谷的铁桥节度、顺州和滇池东滨的拓东,形成了傈僳族明代以前的分布格局。尽管远离故土,盐井尽失,傈僳族与盐的故事远未结束。
3、盐的味道
时光流逝,江山易主,而盐铁榷税带来的利益使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乐此不疲,盐铁官营专卖长盛不衰。食盐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能否正常供应食盐还关乎社会稳定和民生大计,调控食盐成了封建官僚机构的重要行政内容。为防止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发生,历代朝廷都设有管理盐务的大臣,盐务是皇权政治直接参与管理的事务。对盐的开采、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都制定了详细规则,还成立了缉私队严厉打击食盐走私。在滇西北,虽然制定了严密的控制手段和森严的食盐贸易壁垒,但是因为盐的采掘、加工工艺得不到根本改善,食盐的生产能力极其低下,在横断山区山地民族中,食盐历来是稀缺之物。
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后,继续加强盐铁榷税之政,设盐课提举司4个,分驻安宁、黑井、白井、五井(云龙)等产盐地,下设12个盐课司,以提举辖周边盐井,出现中心治所,散漫不相统属的生产点开始形成分区域的集结性生产。为扩大生产能力,也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政策:“正统九年(1445年),令云南各盐课司,每灶添拨余丁2人,免其差役,专一探薪煎盐”。所以生产点逐步增多,除滇中的阿陋、草溪、只旧、元兴等井和滇西的乔后井产盐渐有发展外,还在滇南的西双版纳开辟了磨歇盐井。明代行盐制度为民制、官收、商运、民销。由于内地人口大批移入,汉族人口超过其它民族,加之矿业及其它手工业有一定发展,盐需求量极大增长。因此,明朝皇帝加强了食盐榷税的管理。正德二年(1507年),“令云南盐井官吏,各井盐课务要逐年完纳”,规定一年完不成盐课的官吏,“革去官带住伴”,三年完不成者则官府降格一级,“吏革役为民”。
也就是说,在皇帝的新政下,如果一年内完不成盐课征收,则将革去责任官吏的所有随从。三年完不成盐课的,则集体降级处理,四品知府大人可能变成七品知县芝麻官,衙役可能失去皇帝的俸禄变成平头百姓。皇帝通过盐政将各级官僚机构与人员的利益同朝廷紧密捆绑在一起,因而在云南取得了仅次于田赋的一大税收,“每岁课银3.4~4万两”。尽管云南盐矿、盐井丰富,推行盐铁榷税使朝廷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当时交通不便, 盐的驮运十分艰辛,又有灶户、官府、销商的层层盘剥,到了销售地,盐价昂贵,出现了“斗米斤盐”的价格。在滇南的双江县,50斤谷子只能换回3斤官盐,丽江半斤贝母才能换1斤盐,腾冲要一驮棉纱换一驮盐。人民贫瘠,不胜负担。此政一度延续至民国时期,使横断山区山地民族常年缺盐淡食,在怒江的贡山县竟有平生未尝过盐味的老人。因而,傣族把食盐叫做“白色的金子”,白族把食盐当作结婚的礼品。
清代康熙中叶,云南盐政曾改官销,由于盐价居高不下,穷苦百姓无力购买,而官府又不愿降低价格,导致官盐积压严重,官府不愿让利于民,为“疏稍积压”,朝廷推行“计口授食”的盐政。他们采用按户摊派定价食盐的方法强迫人民购买,即是所谓“烟户盐”。这种苛税政策施行之后,人民往往是“前盐尚在,后盐又到。”横断山区百姓为缴纳盐价,不得已“以后领之盐贱卖以完前盐之课”日积月累,循环往复,人民负担日益沉重,因不堪重负而饮刀自尽、悬梁而亡者“岁岁有之”。面对如此局面,乾隆元年三月皇帝下令:“朕闻滇省盐价昂贵……心深为轸念。查该省盐课,除正项外,有增添赢余,以备地方公事之用,朕思赢余之名,原系出于民食充裕之后,若民食不充,自无仍取赢余之理。著总督尹继善悉心妥办,将赢余一项即行裁汰,务令盐价平减。纵使昂贵,亦只可在三两以下。若裁去赢余之后,公用有不敷处,可另行酌议请旨。”乾隆皇帝觉得云南盐价过于高昂,下令禁止派盐。无奈山高皇帝远,勒派之风依然如故。为了降低盐价,乾隆帝开始着眼于雍正年间耗羡归公后的盐课盈余银。同时规定“云南所产井盐俱系府州县领销,派定额数,由各盐井领运分销办课,不许越界贩卖,通行已久,两迤冲繁之处人民辐輳不难照常销引,间或缺盐借之临近州县通融协济,其山僻州县乡村窎远居民鲜少,地方官恐蹈堕销之咎,关系考成,遂将盐井分派里甲挨户分食,官盐按限缴课,名曰烟户盐……夫盐为小民日用必须之物,虑民远涉,是以因地制宜不徒为销引计也,一则患盐之不足,一则患盐之有余,俱非均平之道,著该督抚,酌量变通悉心妥议,务使官不堕销、民无偏累”。
清廷本想按户销售食盐,试图积极将新开盐井之盐对应销往边远缺盐地区,使得人皆可食,无奈由于官僚机构贪腐严重,“始则计口授食,继则按户分派。始则先课后盐,继则无盐有课”,加之食盐蕴藏的利益,官员私藏强摊食盐者层出不穷。由于供需矛盾加剧和价格居高不下,“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之二十三四等日,蒙化、太和、邓川、赵州、云南、永北、鹤庆、浪穹、楚雄、大姚、元谋、定远、禄丰等处,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蚕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于积薪中,惨不可言。”滇西十三个地区几乎同日爆发农民暴力反抗,围攻盐场、剿杀盐吏,震惊清廷。史称“压盐致变”。事件发生后,清廷云南当局派兵平息,数千民众“伏路号诉”,带兵“大吏”本想用大炮轰击民众,经云南提督苏尔相极力制止,民众才免于葬身炮火之下。云南籍进士谷际岐向朝廷上奏《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一折,痛陈其害,并揭露了“压盐致变”的惨祸,强烈要求改革云南盐政。清廷被迫于嘉庆五年(1800年)改为“民运民销”,但积淀百年的盐的江湖,使得盐的开采、运输、销售长期控制在地方豪酋、土司和官吏之手。嘉庆皇帝的盐政改革,在横断山多民族地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影响。 (未完待续)